三马共“曹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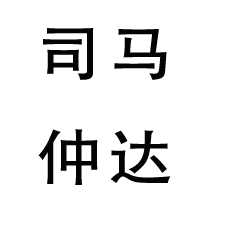
诸葛亮“六出祁山”,与其“对敌”的曹魏“人杰”至少有两位,前有曹真,后有司马懿。曹真字子丹,据称是曹操族人之子,少孤,为曹操收养,视为己子。诸葛亮前两次出师,一次在祁山、一次在陈仓,均为曹真所败。司马懿字仲达,河内温县人。 诸葛亮后两次出师,皆为司马懿所阻。
赤壁之战以前,曹操的主要谋士是荀彧、荀攸、郭嘉、程昱等人;赤壁之战后,司马懿、刘晔、陈群等人逐渐崭露头角。公元215年,曹操占领汉中,当时为丞相府主簿的司马懿随军到汉中,力主进军成都,一举荡灭刚刚入川占了益州的刘备。同为丞相府主簿的刘晔也主张立即取川。:但此时的曹操似乎有些暮气说了一句泄气话:“人苦无足,既得陇,复望蜀邪!” 成语“得陇望蜀”由此而来 。
后来的情报令曹操后悔不迭:当时刘备立足未稳、曹操占汉中,川中一夜三惊,如果乘势进兵,非常有可能把刘备赶出益州。 几年后,刘备占了汉中,关羽围攻樊城,利用汉江大水,全歼于禁率领的曹操援军,“威震华夏”。当时曹操在邺都,汉献帝在许都,曹操想把汉献帝迁到邺都,司马懿坚决反对。这次曹操听从了司马懿的建议,鼓动孙权偷袭南郡,于是有了关羽失荆州、走麦城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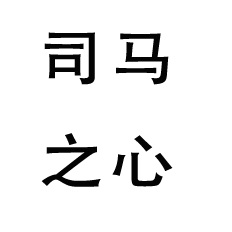
虽然出身、教养、情趣不同,司马懿的性格其实与曹操颇为相似。《晋书》说司马懿:“内忌而外宽,猜忌多权变…有雄豪志。”几乎就是在说曹操。英雄惜英雄,但英雄未必容得了英雄,特别是听说司马懿生理上有个特点的时候。什么特点?身体不动,头可反顾,相术称为“狼顾相”。曹操开始不信,一次司马懿在前走,曹操在后猛喝一声,司马懿一惊,一回头,果然身子不动。曹操大吃一惊。
又有记载说,曹操曾梦见“三马同槽”,三匹马同在一个食槽进食。“槽”为“曹”的谐音,“马”被猜测为司马懿和他的两个儿子:司马师和司马昭。所以,曹操既用司马懿,又忌讳司马懿。 虽然曹操对司马懿有所猜忌,但用人之际,不能仅凭猜忌杀人啊,何况司马懿处事谨慎,不留把柄。
所以曹操也有些迷糊,自己是否过于多心?但还是告诫儿子曹丕,对司马懿要多加提防。这种事情在历史上,乃至在现实中,在政界在商界,在一切权力场,几乎比比皆是。有一种说法,“用人不疑,疑人不用”,但更多的情况是“疑人要用,用人要疑”。也难怪曹操羨慕孙坚的儿子,因为自己的几个儿子虽然各有才华,却没有一个能真正继承自己的事业。
曹丕是舞文弄墨的高手,却不是经世谋国的天才,但有一个长处,敬重高人,不但佩服司马懿谋大事、有奇策,也羡慕司马懿名门望族的身份与教养。所以,不但没有把父亲曹操的警告当回事,还在临死前把儿子曹叡托付给司马懿。
任何一个领域,包括政界在内,有时是靠拼健康、比寿命的。司马懿不但活过了比自己年长一岁的最大的外部对手诸葛亮,也活过了潜在的内部对手曹真、陈群,还活过了比自己小八岁的魏文帝曹丕、小二十六岁的魏明帝曹叡,一直活了七十三岁,为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中的第一高寿。
如此高寿,又富于谋略,更西御诸葛、北定辽东、南退孙权,所以司马懿的威望越来越高。除了封王之外,司马懿享受了曹操在世时候的一切待遇。司马父子的势力如同当年曹操一样,迅速膨胀。司马懿死后,司马师、司马昭相继执政,曹魏的皇帝成了司马父子兄弟的玩偶。但是,曹操的子孙中也有一位血性汉手,名叫曹髦。
曹髦是曹丕的孙子,封高贵乡公。魏明帝曹叡死后,养子曹芳继位。曹芳做了十六年皇帝,八岁到二十三岁,少年到青年,眼睁睁看着曹氏日益削弱、司马氏日益强大,愤懑之情溢于言表。司马师迫使魏明帝皇后即郭太后废去这个越来越不听话的皇帝,打算立魏明帝一兄弟为帝。但是,郭太后对司马兄弟早已不满,废皇帝听你的,立皇帝得听我的,于是立了虽然年仅十四却有血性的曹髦为帝。
几年后,眼见曹姓江山落入司马姓之手,二十岁的曹髦忍无可忍,召集宫中卫士、宦官,当众宣告:“司马昭之心,路人所知也!”司马氏之心,路人皆知。进行了一番“痛说革命家史”的动员后,曹髦拔剑登车,率领这帮乌合之众,找司马昭拼命。司马昭的卫队见皇帝亲自挥剑而来,不知所措。正巧,司马昭的一位心腹贾充赶来,大喝一声:“司马公畜养汝等,正为今日。今日之事,无所问也!”
一声令下,立即有不怕死而且想立功的将领,操戈而上, 把曹髦刺了个直正的“透心凉”。后来追究责任,执行命令的将领被灭了三族,发布命令的贾充却升了官。这应该是此时拥曹派和拥司马派势力斗争的结果。也正是因为这种形势,所以司马昭虽然不但废立皇帝,而且公开宰杀皇帝,这是当年曹操想也不敢想的事情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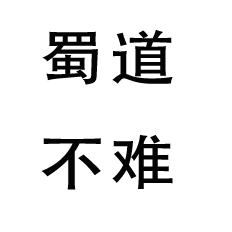
公元263年,刘备死后四十年,诸葛亮死后三十年,司马昭掌控下的曹魏出兵十八万,分三路大举攻蜀:征西将军邓艾率军三万,自狄道(今甘肃临洮)出兵,攻击驻扎沓中的姜维。“沓中”地当甘川古道,在今甘肃岷县南、曲周西,约当著名的“天险腊子口”一带。雍州刺史诸葛绪率军三万,自祁山向南进兵,切断姜维的归路。镇西将军钟会率主力十余万自斜谷、骆谷,即今陕西宝鸡到周至一线,越秦岭、攻汉中。
战争开始的时候按司马昭的部署进行,后来就变得有些出人意料了。邓艾进攻沓中,与姜维形成僵持,诸葛绪切断了姜维的退路,钟会则攻占了汉中。这是司马昭的部署。但是,当得知钟会大军占领汉中后,姜维摆脱邓艾的纠缠,击溃诸葛绪所部,与援军一道,赶赴剑阁,堵住钟会。这样,姜维与钟会纠缠在一起,邓艾没事了。
司马昭决策攻蜀时,长期和姜维交战的邓艾多次上表反对,认为伐蜀时机不成熟。司马昭派专员前往监军,邓艾不得已才出兵;长期在司马昭身边做参谋但并无独立带兵经历的钟会,坚决支持攻蜀。但是,当战事陷于胶着时,主张伐蜀的钟会遇难思退,打算退回汉中;不主张伐蜀的邓艾却知难而进,上书司马昭,请求从阴平小路偷袭涪城(今四川绵阳)。
邓艾认为,如果姜维还军救涪城,钟会可以率军迈着方步向成都进军;如果姜维不救涪城,涪城兵少,“掩其空虚,破之必矣”。涪城一破,成都指日可下。兵贵神速,邓艾一面请示,一面率军向南行军七百里,尽是荒无人迹之处,山高谷深,缺粮断炊,多次陷于绝境,又多次化险为夷。当衣衫褴楼的万余魏军突然出现在江油城外的时候,蜀汉的江油守将惊恐万分,开城而降。
后主刘禅听说江油失守,立即派诸葛亮的儿子、卫将军诸葛瞻督军增援涪城。但是,诸葛瞻虽有才华,却无实战经验;呼声虽高,却名不副实。军到涪城,副将力劝抢占险要,堵截魏军。诸葛瞻却放弃涪城退守绵竹。邓艾又一次意外之喜,直扑绵竹。诸葛瞻杀了邓艾派来劝降的使者,却抵挡不住魏军,和儿子诸葛尚双双战死。 诸葛膽绵竹战死,成都城里乱成一团。有人主张固守,与邓艾决一死战;有人主张放弃成都,投奔孙吴。 刘禅选择了投降,并且命令姜维就近向钟会请降。邓艾第三次意外之喜,竟然兵不血刃占领了成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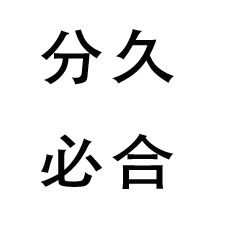
公元265年农历八月,灭蜀后两年,司马昭去世,儿子司马炎继位为“晋王”、“相国”。几个月后,曹魏末代傀儡皇帝曹奂被迫禅位给司马炎。 从司马懿到司马师、司马昭兄弟,再到司马炎,祖孙三代,从排斥曹操到接纳曹魏,从尽心尽力为曹魏办事到算计曹操子孙并最终接管了曹魏政权,三代“马”共“槽”,历时六十年,最终食“曹”。
司马炎从父亲手中继承了巨大的政治财产,三分天下,晋得其二,伐吴成为下一个目标。 公元280年农历正月,晋军六路攻吴,直接结束孙吴政权的,正是“阿童”王濬的“水中龙”。三月十五日,王濬率领的益州水军顺江而下,占领孙吴的都城建业(今南京),吴主孙皓投降。唐代刘禹锡《西塞山怀古》形象地描述了当时战争的大过程:“王濬楼船下益州,金陵王气黯然收。千寻铁锁沉江底,一片降幡出石头。”
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以“天下大势,合久必分”为开篇,而以“天下大势,分久必合”为终结。自公元189年董卓进京,东汉名存实亡,军阀混战、三国分立,百年之后,晋灭吴,重新统一,人们期望着司马炎以其雄才大略,创建起继秦汉之雄风的大帝国。但谁也没有想到,这个统一却是昙花一现,整个中国此后竟然陷于比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更为混乱的局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