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北府”传承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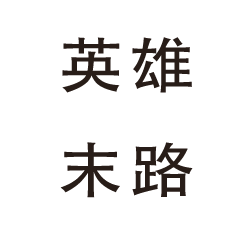
在司马道子父子的折腾下,东晋的各种矛盾激化起来,不但丧失了难得的发展机遇,并且导致了多次动乱,包括王恭的起兵、桓玄的称帝,孙恩、卢循的“五斗米道”暴动,等等。但是,在所有的这些动乱中,有一支军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它支持谁,谁就打胜仗;背叛谁,谁就得垮台。
那么,这是一支什么军队?就是在“淝水之战”中起着重要作用的“北府兵”。 有一位人物和“北府兵”紧紧连在一起,这就是刘牢之。“淝水之战”后,谢玄率军北伐,刘牢之率领的“北府兵”独当一面,收复了许多地区,但后来在和鲜卑慕容垂的战争中失利,谢玄、刘牢之都被召回。
“淝水之战”的前后,刘牢之和他的“北府兵”由谢玄指挥,而且,这支军队本来就是谢玄组建的。但是,和谢石、谢玄出身士族,有着广泛的上层关系不同,刘牢之却是从底层打拼上来的将领,有搏击技能,有军事谋略,却没有政治眼光。失去了谢玄的领导之后,在错综复杂的东晋动荡中,刘牢之顿时失去了政治方向,一面带着“北府兵”东征西伐,一面不断地投靠主人又背叛主人。
第一次投靠和背叛。北伐失利被召回后,刘牢之被镇守京口的王恭招至门下,这京口也是“北府兵”的基地。王恭起兵讨伐司马道子,刘牢之率领“北府兵”为前锋。 由于门第的观念,王恭并没有真正尊重刘牢之。而因为战功卓著,名气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的刘牢之,也越来越在乎别人对自己的态度。司马道子的儿子司马元显虽然只有17岁,政治上却比王恭、刘牢之成熟得多,他看出了二人之间的矛盾,许诺高官厚禄。刘牢之临阵倒戈,王恭兵败被杀。
第二次投靠和背叛。 桓温的儿子桓玄从荆州起兵,要和司马道子、司马元显父子争夺对东晋的控制权,司马元显命刘牢之率“北府兵”火速迎敌。刘牢之舅舅受桓玄的派遣,充当说客。 于是,刘牢之决定倒戈,投靠桓玄。刘牢之一倒戈,司马道子、司马元显父子玩完了,一个流放之后被杀,一个当即被杀。
第三次投靠和背叛。为了避免自己和王恭、司马元显一样的下场,桓玄决定夺了刘牢之的兵权。 于是,命刘牢之为“征东将军、会稽太守”让他离开京口。刘牢之虽然投靠了桓玄,心里也不十分踏实,只是觉得自己手上有军队,谁也奈我不何。你桓玄玩花样,就干了你。桓玄果然玩花样,要夺自己的兵权,刘牢之召集众将商议,打算再反桓玄。
但反了桓玄投靠谁?没有下家,也就没有方向。刘牢之打算去江北,那里曾经是自己的发迹之处。但刘牢之的打算引起了更多人的反对。于是,大家散伙了。 “北府兵”在东晋后期是“胜利”的代名词,刘牢之的一生荣辱与“北府兵”紧密相连。北府兵的主要将领离他而去,刘牢之就不是刘牢之了。既没有军事力量又没有政治方向的刘牢之,看不到前途、看不到希望,只好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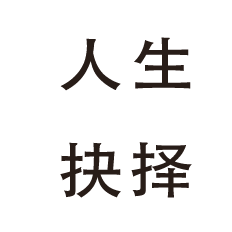
刘裕有一个华贵的家族谱系,为汉高祖刘邦的弟弟、被封为楚王的刘交的第二十一代孙,世居当年“楚国”的都城彭城,即今徐州。 谁也没有想到,热衷于赌博的刘裕竟然和反对赌博的陶侃一样,对东晋有“再造之功”。而刘裕能够出人头地,是因为有孙恩的暴动,又是一个“乱世出英雄”的老套故事。
公元399、400年之交,东晋朝廷派谢安的儿子谢琰和刘牢之率领“府兵”东征孙恩,刘裕投奔到刘牢之军中,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。 对于刘裕个人和这个时代来说,是一个重大的人生抉择。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,投身“北府兵”的刘裕屡立战功,得到刘牢之的信任,迅速成为“北府兵”的重要将领。
公元402年,桓玄起兵,进攻南京,刘裕随刘牢之奉命讨伐。但是,刘牢之不顾刘裕等人极力反对,先是归附桓玄,旋而背叛桓玄。刘裕再次做出了人生抉择,放弃了“反覆”的刘牢之,和何无忌一道返回京口,虽然继续隶属于桓玄,却保持相对独立。
公元403年年底,桓玄称帝,改国号为“楚”。称帝之前,专门派人联络刘裕,争取支持。由此可见刘裕在桓玄心目中的地位了。刘裕怎么办? 刘裕一面应付桓玄,一面暗中联络散布在京口、扬州等的“北府兵”诸将领,约定共同起兵,讨伐桓玄。
由于作战勇猛,又长于谋略,特别是关键时刻有定见,刘裕被众人推为盟主。经过两个月的激战,桓玄兵败被杀,刘裕把被桓玄所废的晋安帝迎回南京复位,“再造晋室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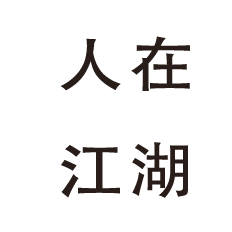
回到南京的晋安帝为了感谢刘裕“再造晋室”之功,发表长篇诏书,将刘裕比之为商之伊尹、周之姜子牙,称为“尚父”,晋位侍中,都督中外诸军事。刘裕由“北府兵”的将领,成为东晋实际上的统治者,可以说是“功德圆满”。 但是,刘裕的步子停不下来,各种因素在推动他继续前行。
有哪些因素呢? 第一,士族衰落,皇室衰微。曾经代表着东晋“均衡”格局一极的皇室司马家族,经过司马道子的折腾,特别是经过桓温的废立、桓玄的取代,不但政治势力荡然无存,也失去了精神上的意义。刘裕成为这个将倾大厦的唯一支柱。
第二,江南动荡,处处用兵。在当时的荆州、益州等处,仍然有桓玄的余部及其他割据者,这些割据势力与“五胡十六国”中的“后秦”“南燕”等相互联络,对东晋构成威胁。孙恩死后,妹夫卢循组织了更为庞大的队伍,继续与东晋对抗, 如果没有刘裕,这些势力难以铲平。可以说,此时的刘裕和他的军队,已经成为东晋这座行将坍塌的大厦的擎天柱,也是江南地区唯一能够掌控局面的势力,刘裕本人也只能在权力中心继续前行。
第三,同盟分化,主盟不易。 在讨伐桓玄的战争中,刘裕的角色和当年平定苏峻的陶侃一样,并非全军统帅,而是多股势力的“盟主”。 这是一支真正的“盟军”,这支盟军至少由十来股力量组成。可以说,这是一个以“北府兵”将领为主体的名单,可以视为刘牢之死后,“北府兵”的重新集结。
但是,他们并非刘裕的“属下”而是“战友”。 将领之间,并没有绝对的“领导人”,威望相对高一些的刘裕,只是暂时“主盟”。随着桓玄的平定,刘裕的威望迅速飙升,这个同盟也迅速分化,大多数人成了刘裕的“下属”,如何无忌、刘敬宣、檀道济等,也有人公开分庭抗礼,成为刘裕的对手,如刘毅等。
刘裕要成为“北府兵”的真正统帅,还有待时日。但是,除了刘裕,这个局面一时还无人能收拾。刘牢之、刘裕都可以说是“乱世英雄”,而且都是以“北府兵”起家,但一个成功,一个失败,固然有种种客观因素,但一个人的“见识”却往往在其中起重要的作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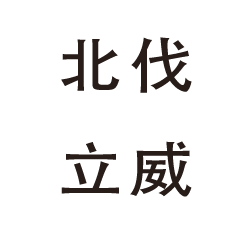
平定桓玄之后,刘裕本来可以用更多的精力打点江南,巩固自己的地位。但是,任何一个地区的政治形势,都不是孤立存在的。“国际形势”推动着刘裕把目光和精力投向了北方。“淝水之战”后,前秦迅速崩溃,崩溃的过程中,苻坚曾向东晋告急求救;而在东晋内乱中的失败者,也常常逃向北方寻求保护。
公元409年农历四月,刘裕率军北上,经淮河入泗水,直抵下邳,然后弃舟登陆,进入今山东境内,这里是南燕的地盘。南燕军队集结在广固东南的临朐,万余铁骑,等候晋军的到来。刘裕这次北伐,显然做过精心的准备,特别是对付骑兵的准备。
晋军的主力,仍然是“北府兵”,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等将领都在军中。晋军带有兵车四千辆,分为左右两翼,结阵而行,抗击燕骑的冲击;每辆战车配步兵若干名,手持长矛,寻机刺杀燕兵。双方苦战,进入胶着状态。刘裕的骑兵绕至阵后,直扑临朐城。临朐失守,燕兵大乱,刘裕亲自击鼓,晋兵士气大振,燕兵败回广固。
燕主慕容超乘坐的马匹、车辆,以及代表身份的玉玺、豹尾等,都被晋军缴获,刘裕命人将其送回南京。战争还没有结束,这些东西送去南京干什么?还是两个字“立威”。 晋兵乘胜推进,攻破广固外城。慕容超固守内城,晋兵筑起长围对峙,双方打起了持久战。
经过整整半年时间的围困,晋兵终于攻破广固内城,慕容超突围被俘,送往南京斩首。刘裕的这个举动,目的还是两个字:“立威”。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,刘裕灭卢循,平定“五斗米道”的暴动;出兵荆州、益州,攻灭当地的割据势力。公元417年,刘裕再次出兵北伐,经过多次激战,取洛阳、占长安,在当年八月,灭了羌人所建的后秦,后秦“皇帝”姚泓被俘,仍然是押送南京,斩首示威。
从公元316年刘曜攻占长安、西晋灭亡,长安这座古都先后成为后赵、前秦、后秦的都城,一百年后,由刘裕率领的以“北府兵”为骨干的晋军攻占,在当时是大大增了汉人的志气。东晋疆域,也在这个时候达到极盛“复国”的梦想,也眼看就要实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