盛衰之间

苻坚的前秦调集军队大举南下,意欲一举灭晋,统一中国。东晋也派出军队,与在寿阳一线的前秦军形成对峙。从当时的整体形势看,毫无疑问是秦强而晋弱。前秦调动了多少军队?据记载是骑兵27万、步兵60余万,近90万。那么,东晋调动多少军队?8万人,由谢石、谢玄率领。双方兵力是90:8。
出于对形势的担忧,统帅上游荆、江诸州军队的桓冲,提出派三千精锐赴南京,加强京城的防务;在江北正面防御前秦的谢玄,也专门来到南京,请叔叔谢安面授机宜。但是,谢安传递给他们的,只有两个字:镇静。这两个字传递给谢石,谢石打算坚守,以劳前秦之师、以待前秦之变。
这边晋兵在策划,那边前秦在行动。当时苻融的前锋已经渡过淮河,攻占了淝水之西的寿阳,即今安徽寿县,在分出数万人往西线之后,又派出了一支两万人的部队 ,推进到洛涧以西,作为前哨。洛涧以东不远,就是晋军的大营了。
公元383年农历十一月,谢石在谢玄、谢琰的力劝之下,决定首先打击这股秦军。打头阵的自然是“北府兵”,领兵的是“北府兵”的将领刘牢之。
前秦军列阵于洛涧之西,要看看传说中不堪一击的晋人面对“我军”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。没有想到的是,还没有真正看清晋军的士兵、晋军的将领是什么样子,刘牢之就带着五千“北府兵”,呼啸着渡过洛涧,朝前秦军扑来。
“两军相遇勇者胜”,冷兵器时代尤其如此。前秦军虽然说久经大敌,但也有多年没打硬仗,加上轻敌,被不要命的“北府兵”杀得人仰马翻,主将被杀,全军溃散,阵亡万余人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“淝水”之战,在淝水东边不远的“洛涧”拉开了序幕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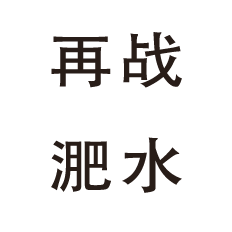
初战告捷,谢石、谢玄、谢琰挥师而进,直逼寿阳,与前秦军隔着淝水对垒。败兵逃回寿阳,苻坚大吃一惊,和苻融一道,登上城墙。但见晋军部伍严整,显然是训练有素的精兵,有点出乎意料。不经意间一拾头,但见远处东北方向的八公山上,隐隐约约都是晋兵。 苻坚在精神紧张之中,错把八公山上繁盛的草木当成了晋兵。 “草木皆兵”的成语,即此而来。
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根据各方面的记载,对发生在“淝水”的前秦与东晋之间的这次战斗的过程做了描述, 整个过程可以分成以下几个片段:第一个片段。决战在即,前秦近20万军队布列在淝水的西岸,严阵以待。谢玄为先锋,领着东晋军在淝水的东岸,与前秦军隔河布阵。双方僵持。
第二个片段。晋军的前敌指挥谢玄派人去见秦军的前敌指挥苻融,提出: 贵军是客,我军是主,我军先退一步,让贵军渡河。贵军渡河之后,我们决一死战。苻融怎么个态度?当然不能同意,把我们氐人当傻瓜啊!你们汉人的兵法,有“半渡而击之”的说法,别以为我们不知道!等我军渡一半,甚至不到一半的时候你发动进攻,我不是吃大亏了吗?
谢玄的使者换个角度,说贵军如果对我军先退、贵军渡河有疑虑,那贵军先退一步,让我军渡河怎么样?苻坚觉得这样最好,面前的这支晋军是劲敌,不好打,用汉人“半渡而击之”的兵法打汉人,这倒是个好机会。 于是,苻坚同意了,但这正是谢玄所需要的,他要的就是已经布阵的前秦军的挪动。
第三个片段。 战事完全按谢玄的预计而不是苻坚的愿望发展。前秦军刚刚挪动,晋军就渡河了。 当时正是枯水期,晋军应该早已勘察好水情,哪些地方需要用船,哪些地方可以徒步瞠水。所以,这边前秦阵脚刚动,那边东晋兵就鼓噪而来,乘船的、瞠水的,转眼间杀到眼前。
前秦的前军因为后撤乱了阵脚,被晋兵杀晕了头;后面的军队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,有想上前的,有想后退的。结果,人挤人、马挤马,人踩人、马撞马,乱成一团。苻融拼命想挤出来指挥部队,马却被绊倒了,为晋兵所杀。
这个时候,朱序领着本部人马,一边后撤,一边高呼:“秦军败了!”后面的前秦兵以为前面败了,争先恐后而逃;前面前秦兵本来就晕了头,前有晋兵杀来,后面的弟兄又跑了,于是由后退变为败逃。自相践踏死的、被晋兵杀死的、饥寒交迫死的,尸体“蔽野塞川”(《资治通鉴》)。
晋兵继续追杀,秦兵拼命奔逃,耳边听到的风雨声、鸟叫声,都当成了晋兵的喊杀声,因而有“风声鹤唳”的成语。苻坚身上中了流矢,由亲兵保护拼命北逃。中国历史上又一次著名的战争,“淝水之战”,以晋军的完胜、前秦的溃败而告结束。谢玄趁势指挥军队迅速向北抢占地盘,收复了黄河、淮河之间及秦岭以南的许多地区,东晋的疆域,达到极盛,也为后来的“南朝”开创了一片天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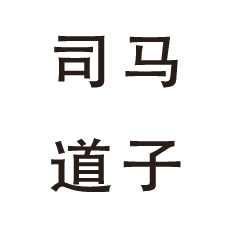
淝水之战后,北方的威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得到缓解,南方的经济、文化得到比较快的发展。 这个时候的东晋,无论是谢安还是其他的士族、庶族,以及普通民众,更盼望早日结束战争,过安稳的日子。
淝水之战的第二年,南京上游的桓冲去世,第三年,主持东晋朝政的谢安去世,东晋在短时期里,失去了两位德高望重又能够协调各方利益的政治领袖。而谢安还没有去世的时候,权力已经被剥夺。谁剥夺他?司马家族,代表人物是司马道子,他的助手和心腹,则是谢安的女婿王国宝。
司马道子是把谢安拉入政治的东晋简文帝司马昱的儿子,是谢安执政时在位的孝武帝的同母弟弟。 淝水之战后,司马道子开始谋求更大的权力了,主要的对手就是老资格政治家谢安。谢安执政多年,谢氏兄弟子侄多在军中效力,要找茬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?加上还有谢安的女婿王国宝提供内幕。
这位王国宝的身份特殊。 王国宝不但门第高,而且觉得自己有本事,一般的职务、具体的事务,看不上眼。但偏偏自己不争气,既贪图利益,行为又检点,不但引起岳父谢安的厌恶,不给他提供机会,舅舅范宁也对他极为反感,所以王国宝就投靠了司马道子,为司马道子出谋划策,把谢安挤出南京。
谢安死后,司马道子成了东晋的执政。其实,谁执政并没有关系,只要你干正事。但是,这个司马道子却不干正经事,正是因为他的折腾,葬送了东晋的大好时光,甚至把东晋送进了坟墓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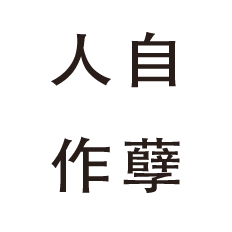
《尚书·商书》说:“天作孽,犹可违;自作孽,不可逭。”中国历史上的动乱,无论是阶级斗争的动乱还是民族斗争的动乱,其根源大多来自汉族统治阶级和既得利益者的折腾,西晋如此,东晋也是如此;谢安之前的东晋如此,谢安之后的东晋也如此。这就叫“人作孽,不可逭”。
司马道子及其亲信的折腾,引发了种种的矛盾。第一,司马道子和孝武帝兄弟君臣之间的矛盾。司马道子不但喜欢纵酒穷欢,还喜欢揽权、喜欢敛财,但并无治理国家的手段,手下王国宝等一批心腹也是乘机揽权、大肆捞钱,形成了一个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共同体,早已引起各大家族乃至太原王氏家族中的某些势力的不满,不断有人上书要求给予惩治。
当孝武帝看着司马道子顺眼的时候,认为这些批评是吹毛求疵;但看着司马道子不顺眼的时候,觉得这些批评太有道理了。于是,一面削夺司马道子权力,一面扶植亲信,制衡司马道子。这样,不但引起司马道子的不满,也严重限制了王国宝等人的利益,这帮人和司马道子结成死党,对抗皇帝及其亲信。
在这场博弈的过程中,孝武帝竟然被一位姓张的贵妃杀了,儿子安帝继位,司马道子得以继续掌权。但是,杀了皇帝的张贵妃竟然下落不明,这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个奇案。
第二,东晋政权和士族及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。 “淝水之战”一结束,孝武帝便用司马道子取代谢安,逼着谢安离开南京,并且削弱上流桓氏的力量。但是,几乎每一次在和士族的斗争中,都以东晋皇室的失败而告结束,皇室的脑袋一伸出来,就被士族打回去。
司马道子掌权的时候也一样。一位和王国宝同出于太原王氏的著名人物王恭,以诛杀王国宝为名,从京口起兵。司马道子无力抵抗,只有处死王国宝,向王恭交代。而桓温的儿子桓玄却从荆州起兵,攻占南京,诛杀了司马道子父子、废了晋安帝,自行称帝,改国号为“楚”。
第三,东晋政权和基层社会的矛盾。由于士族力量的强大,东晋中央政权真正能够控制的地区,主要是“三吴”,即现在的江苏苏州,浙江湖州、嘉兴、杭州、绍兴、宁波一带。这里即是东晋的“后方”,是财赋所出之地。
司马道子父子为了加强南京一带的防卫力量,下令征发三吴地区已经免除奴仆身份的民户,称之为“乐属”,强行迁徙到南京,充当兵役,结果引起这些地区民众的反对。当时的东南一带,“五斗米道”十分流行,首领孙恩、卢循正以“五斗米道”发动民众、对抗朝廷。
朝廷征发“乐属”,把大量免去奴仆身份的民户,以及受到利益侵害的农民乃至地主推向了孙恩、卢循,迅速演变为民众的暴动。这场暴动前后延续了十多年,席卷现在的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、江西、湖北及安徽、江苏的长江以南地区。
虽然王恭、桓玄最终都兵败被杀,孙恩、卢循也先后战死,但在这两场动乱的双重打击下,东晋政权迅速瓦解,作为东晋政权支柱的北方士族势力,也在这个过程中,损耗惨重。